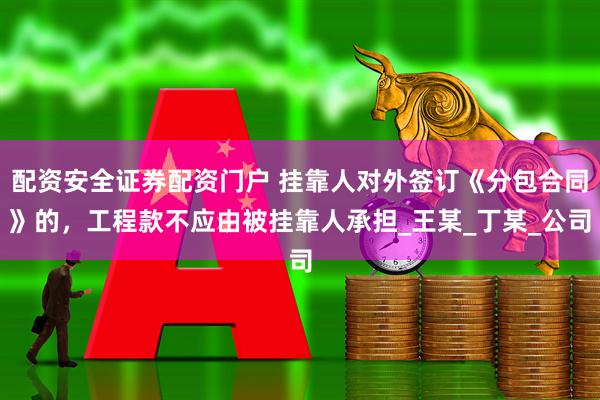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民商事研究院配资安全证券配资门户
文章/杨晋华
一、案例检索(一)案情简介
2013年11月15日,K公司与丁某签订《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由丁某承揽案涉项目,并按总造价0.8%向K公司交纳管理费。2014年3月20日,J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丁某作为案涉项目的负责人,负责合同签订、工程管理等事宜。2014年5月11日,丁某以“建设工程项目部”名义,与王某签订《分包合同》,将案涉项目中的温泉宾馆及接待中心工程分包给王某施工。2014年6月13日,案外人G公司与K公司签订《温泉小镇建筑施工合同》,约定将案涉项目发包给K分公司承包施工,丁某为项目负责人并签字确认。2014年11月15日,丁某与王某签订《补充协议》。2015年5月21日,丁某与王某签订《清算协议》,载明:根据双方友好协商,甲方(丁某)支付我方(王某)12500000元工程款,支付劳务分包单位1800000元误工费及机械、钢管租赁费(此费用不包含劳务单位模板、木方等材料费用);合计14200000元;该合计总金额为最终结算金额。2015年6月30日,丁某向王某出具《证明》,载明“温泉宾馆及接待中心,由王某承建,到目前为止,共计借支项目部工程款伍佰万元整”,王某于2015年7月2日在该《证明》上签署“认可此金额”的意见。2015年7月21日,G与K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温泉小镇建筑施工合同)》,约定双方自愿解除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温泉小镇建筑施工合同》。因丁某未按约定向王某支付工程款,王某将K公司、丁某诉至法院,要求该两方承担付款责任。
展开剩余75%(二)裁判要旨
案件争议焦点:K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某支付工程款;王某主张的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
1. K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某支付案涉工程款的问题。
因K公司与王某之间并无合同法律关系,而K公司与丁某、丁某与王某之间有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要确定K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某支付案涉工程款,需首先明确丁某在案涉项目建设中的身份。 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丁某先于2013年11月15日与K公司签订《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由丁某担任项目负责人承揽案涉项目,并按工程总造价0.8%向K公司交纳管理费。之后,K公司作为承包人于2014年6月13日与发包人G公司签订《温泉小镇建筑施工合同》,约定K公司承包案涉项目,丁某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该合同上签字。从前述约定的内容看,丁某系借用K公司资质承包案涉项目,并向K公司交纳相应的管理费。2014年5月11日,丁某以“G公司温泉小镇建设工程项目部”名义与王某签订《分包合同》,将案涉项目中的温泉宾馆及接待中心工程分包给王某施工。2014年11月15日,丁某又以个人名义与王某签订《补充协议》,在《分包合同》基础上对相关款项使用事宜进行了约定。2015年5月27日,丁某与王某签订《清算协议》,就王某施工的案涉项目温泉宾馆及接待中心的已完工程进行了结算。《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及建工司法解释第四条关于“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分包合同》的主体虽为J公司和王某,但从《补充协议》《清算协议》均系丁某以其个人名义与王某签订,且未设置J公司的权利义务,工程结算也由丁某与王某进行;G公司否认与聚安源公司签订合同;K公司否认将案涉项目转包或分包给J公司,J公司自认未参与过案涉项目的施工和管理;可以认定与王某签订《分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实际为丁某,而非J公司。尽管案涉《分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但合同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相对性不因合同无效而受影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丁某向王某支付工程款。K公司与王某并无合同关系。
2.关于王某主张的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如前所述,丁某系向王某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主体。虽然《分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但王某已就《分包合同》项下的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丁某与王某就王某已完工程签订的《清算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达成结算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属有效,丁某应该按照《清算协议》的约定向王某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清算协议》确定了工程款数额,并约定“本协议商定的工程清算费用双方不得再依据任何理由增减费用”。《清算协议》签订后,丁某于2015年6月30日出具《证明》确认,王某承建了温泉宾馆及接待中心工程,至丁某出具《证明》时,王某共计借支工程款5000000元整。王某于2015年7月2日在《证明》上签注“认可此金额”。前述事实表明双方实际履行了《清算协议》。一审法院依K公司申请、经王某同意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就王某已完成施工的工程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在丁某与王某就已完工程签订《清算协议》、丁某未否定结算结果且丁某未同意并参与鉴定的情况下,不宜以鉴定机构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作为认定丁某欠付王某工程款数额的依据。丁某应当按照《清算协议》确定的结算金额向王某支付6100000元剩余工程价款(结算总金额14200000元-王某自认收到的5000000元-王某自认转让给案外人的债权3100000元)及相应利息。 鉴于K公司再审请求维持一审判决,K公司的前述意思表示构成债务加入。故一审判决判令K公司在3418812.23元工程价款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予维持。
二、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对因该项承揽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 缺乏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请求出借方与借用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资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律师说法在建设工程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就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造成的损失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于拖欠工程款的情形,被挂靠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并无规定,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被挂靠人主张付款责任?挂靠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因其隐蔽性,于实务操作中难以精准识别,尽管相关部门已多次明令禁止,但此现象依旧顽固存续、屡禁不止。对于挂靠人借用被挂靠方的资质成功承揽建设工程后,又将所承揽工程违法分包或转包给第三方施工,被挂靠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从形式上的签约主体、签约时的具体情况及签约后的履行情况综合分析判断。具体而言,如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签订合同,并在签订合同时挂靠人出示被挂靠人的授权委托书、合同上加盖了被挂靠人公章或项目部印章,被挂靠人参与了合同的履行过程等等配资安全证券配资门户,使实际施工人有理由相信挂靠人系代表被挂靠公司,则被挂靠人需要承担付款责任。反之,如挂靠人系以自己名义将工程分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实际施工人建立合同关系的是挂靠人,则被挂靠人通常不需要承担付款责任。本案中,《补充协议》《清算协议》均系丁某以其个人名义与王某签订,且未设置J公司的权利义务,工程结算也由丁某与王某进行;G公司否认与J公司签订合同;K公司否认将案涉项目转包或分包给J公司,J公司自认未参与过案涉项目的施工和管理;可以认定与王某签订《分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实际为丁某,而非J公司。
发布于:陕西省汇盈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